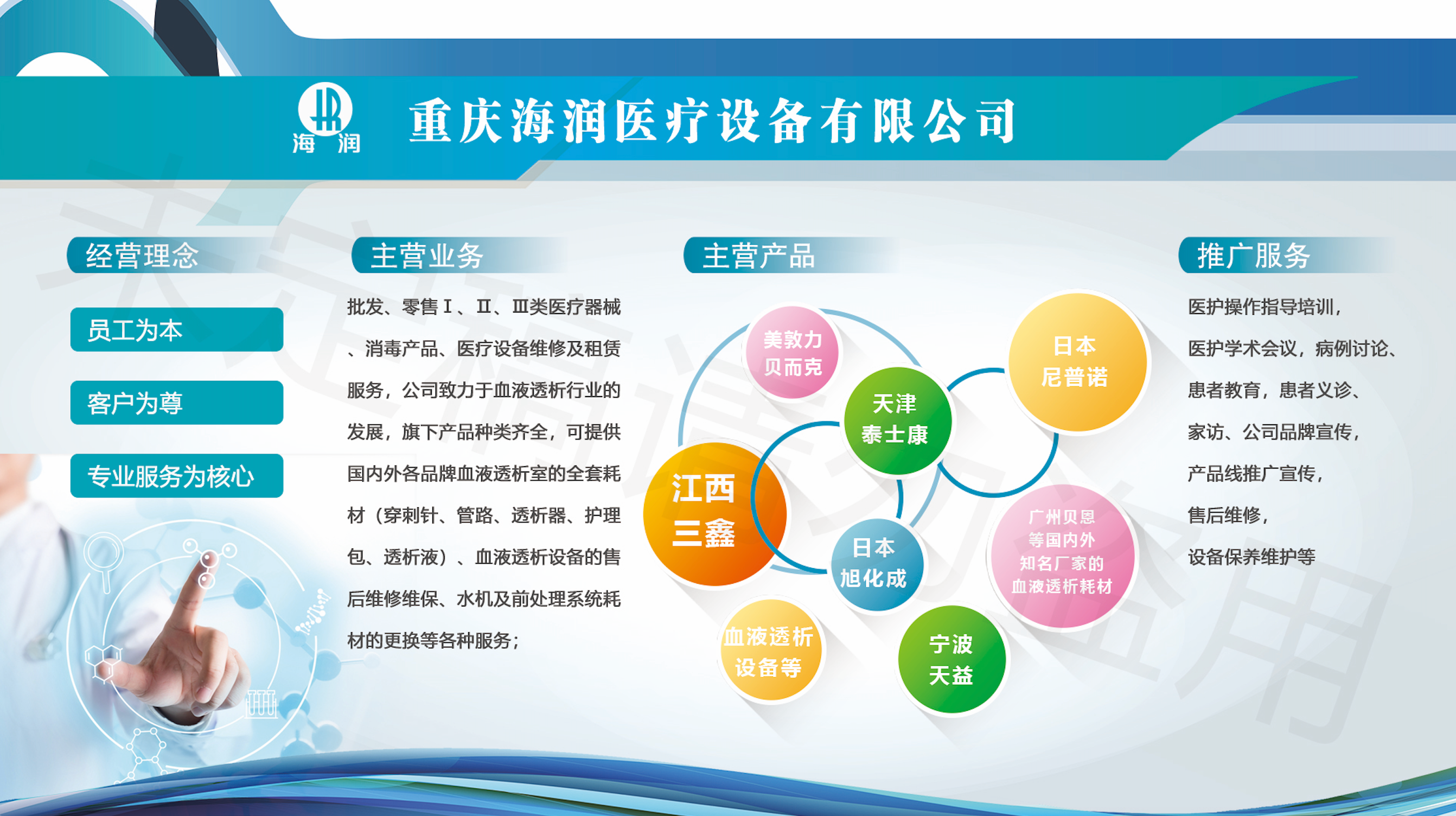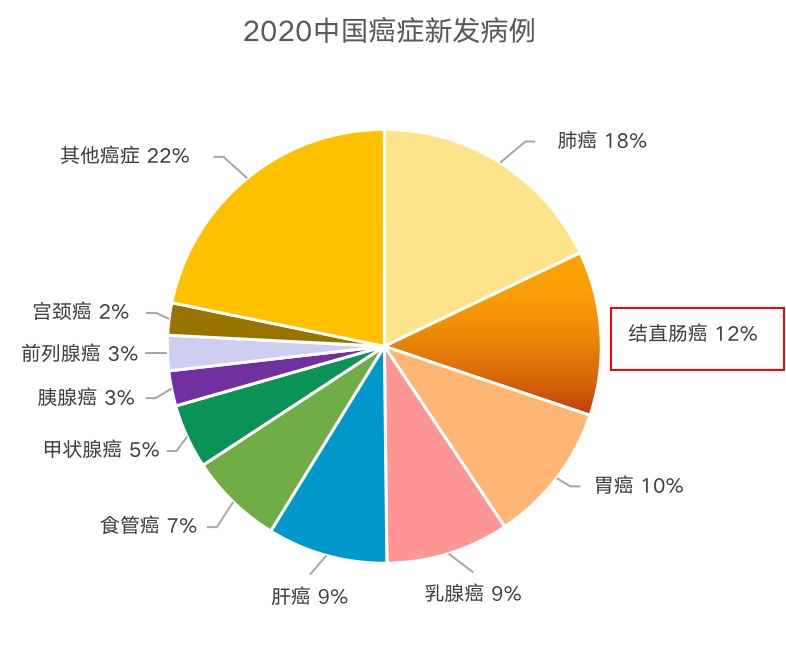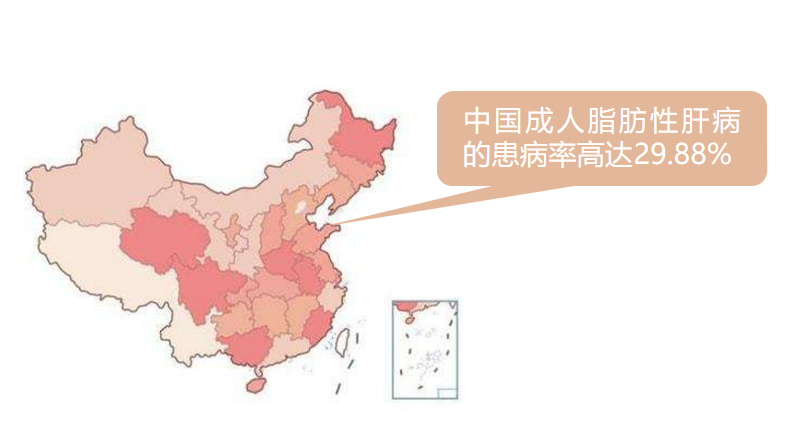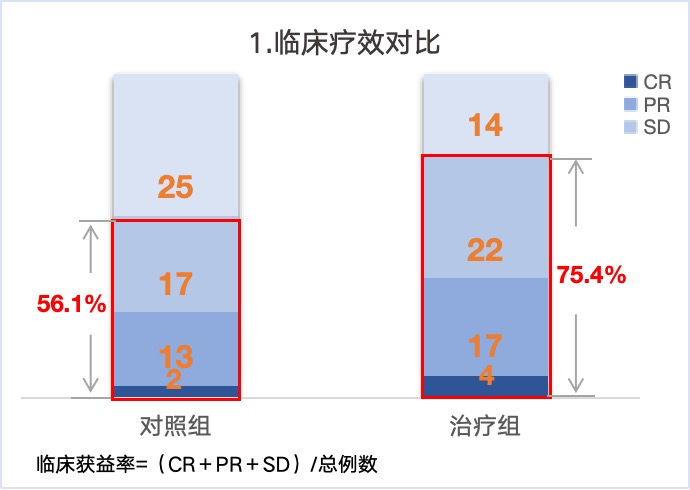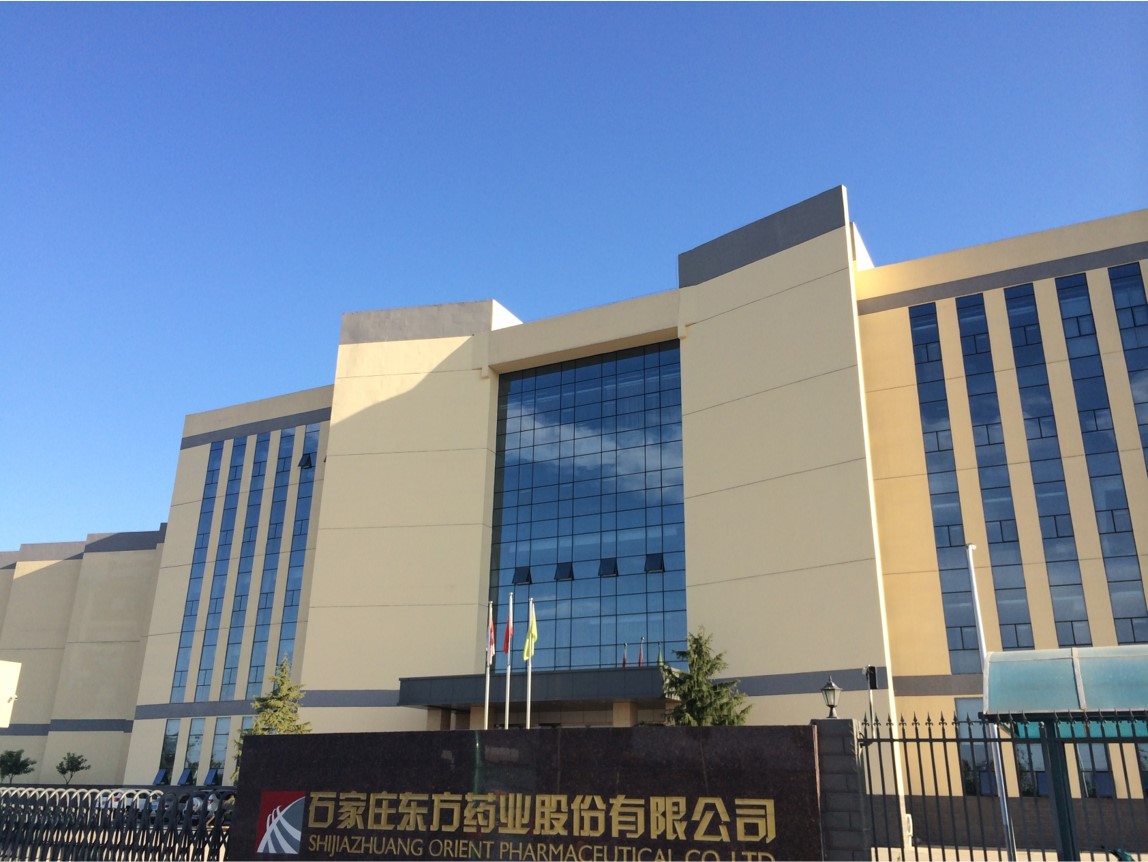当生物学家路易斯·赞布拉诺(Luis Zambrano)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他为自己描绘了距文明几英里远的地方,也许是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某个隐蔽角落发现了新物种。相反,在2003年,他发现自己在墨西哥城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区被污染,阴暗的运河中计数两栖动物。这项工作有其优势:他在家中工作了几分钟,研究了墨西哥的国家标志性ar(Ambystoma mexicanum),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知名的sal。但是在第一年,赞布拉诺就等不及了。
他说:“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就讨厌这个项目。”一方面,“泪不能”抓住任何东西?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确实抓住了一些a。他的发现使他感到惊讶,并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1998年,第一项对a进行计数的稳健研究估计,霍奇米尔科1每平方公里大约有6,000种x。扎姆布拉诺(他现在是墨西哥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的教授)在2000年发现,每平方公里的动物数量已减少到1,000只。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00;如今,由于污染和入侵性掠食性动物的侵袭,每平方公里只有不到35只动物1。
在唯一的自然栖息地墨西哥城的运河中,a已经濒于灭绝的边缘。但是尽管野外可能只剩下几百个人,但在世界各地的家庭水族馆和研究实验室中却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人。它们在人工饲养下繁殖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日本的某些餐馆甚至为它们油炸。
记者Shamini Bundell调查了野生a的命运。
下载MP3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生态学家理查德·格里菲思斯(Richard Griffiths)说:“ x虫是一个完全的保护悖论”,他招募了赞布拉诺参加该项目。“因为它可能是宠物商店和实验室中分布最广的两栖动物,但在野外却几乎灭绝了。”
这给生物学家带来了问题。由于其独特的生理学和显着的再生断肢的能力,olo已成为从组织修复到发育和癌症等所有领域的重要实验室模型。但是经过近百年的近交繁殖,圈养种群易患疾病。而且由于野生x的种群减少,遗传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科学家在学习有关动物生物学的一切知识时会迷失方向。
随着实验室科学家继续研究圈养动物及其庞大而复杂的基因组,Zambrano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正在竭尽全力保护野生动物。他们正在繁殖a并将其释放到霍奇米尔科及其周围的控制池塘和运河中,以观察它们的生长状况,并希望保留其某些自然遗传多样性。拯救它们的任务很艰巨,但是鉴于动物的抵抗力,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墨西哥政府只参与这一过程。
赞布拉诺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了这些巨大的任务是可能的。”“他们能做到吗,为什么我们能做到?”
永不长大的生物
与该地区的其他species物种相比,的进化相对较新,它们在墨西哥中部山区的特克斯科科湖畔兴旺发展。它们是新手性的,这意味着成虫保留了仅在类似物种的少年中才能看到的特征。尽管其他sal变成了陆地生物,但,仍坚持其羽毛状g,并一生都在水中呆着。好像他们永远不会长大。
十三世纪的某个时候,特斯科科湖被墨西哥人(欧洲人称为阿兹台克人的居民)定居。他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由一个建在湖中央的岛屿城市控制。随着帝国的发展,土地也随之增长,在1521年西班牙征服西班牙之后,土地的扩张速度大大加快。如今,阿索洛特尔栖息地的所有剩余部分都是横跨墨西哥城南部Xochimilco的约170公里的运河(参见地图)。
该物种可能已经完全在殖民统治下灭绝了,只是其奇怪的无法生长的特性引起了欧洲科学家的注意,他们在19世纪后期对它感到困惑。
墨西哥的游客把这些生物带回来,并开始繁殖它们。事实证明,该动物是进行研究的理想选择:它在实验室中繁殖容易,是顽强的幸存者,易于照料。x具有大的细胞,可以简化对发育的研究。他们的卵几乎是人的30倍。在an的胚胎中,神经板细胞(即大脑和脊髓的前体)的体积几乎是其600倍。
同样,a的色素沉着在一个细胞与另一个细胞之间变化很大,这不同于人类或其他动物的细胞特征趋于一致。这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追踪胚胎中的哪些组织成为哪些器官。然而,它的基因组很大(大约是人的十倍),这使得在某些方面进行研究具有挑战性。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发育生物学家戴维·加德纳(David Gardiner)说:“这不是一个好的遗传模型生物,但它确实可以再生,这使其成为了不起的生物学模型。” 。
在二十世纪初期,a是了解脊椎动物器官和功能的关键。他们帮助科学家们揭开了人类脊柱裂的病因,即脊柱不能正确形成的先天缺陷。他们在甲状腺激素的发现中发挥了作用:在1920年代,科学家从家畜中将甲状腺组织喂入了a。如果组织已经在分泌激素,则a将变质,失去g,脱落幼虫皮肤。
在1980年代,轴突帮助科学家开发了一个模型,解释了细胞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胚胎中。“振铃状态分裂器”模型提出,许多干细胞通过像胚胎一样的牵拉和拉伸波变成体内的特定组织。科学家发现,他们可以看到轴突细胞在形成组织之前被挤压并伸展。最近,在2011年,来自x虫卵母细胞的提取物已被用于通过启动肿瘤抑制基因2来阻止乳腺癌细胞增殖。
但是,a对科学的最令人着迷的贡献可能是再生医学。这些动物可以长出缺少的四肢,尾巴,器官,眼睛的一部分甚至大脑的一部分。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尽管是新手症,但它们的胚胎阶段仍保留了一些特征,尽管其他sal似乎也可以成年后再生。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再生研究员Tatiana Sandoval Guzm谩n说,生物学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尝试寻找其再生能力背后的机制。他们这样做吗?他们拥有我们不拥有的是什么?或者相反,“哺乳动物阻止了什么?” / p>
Sandoval Guzm谩n对骨骼和肌肉的再生很感兴趣,并接管了德累斯顿一家历史悠久的a实验室。她是一名墨西哥人,在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附近上学,她从没对这种动物有太多的想法,当然也从未考虑过研究它,直到她来到德国。如今,她被这种生物所吸引,并表明3 3再生的许多机制(例如涉及肌肉组织干细胞的机制)与人类所发现的机制并没有太大不同。
大多数再生研究的重点是在断肢的伤口上形成的“残留”或“胚细胞”。人体的这种伤口被皮肤组织覆盖,而a将附近的细胞转化为干细胞,并从更远的地方募集其他人聚集在伤口附近。在那里,细胞开始形成骨骼,皮肤和静脉的方式几乎与动物在卵内发育的方式相同。每个组织都贡献自己的干细胞。
研究人员表明,在妊娠的头三个月中,一种叫做转化生长因子-β的蛋白质对于x的再生和预防受伤的人类胚胎中的疤痕组织均至关重要。尽管人类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失去这种能力,但成年小鼠和人类可以再生指尖,这表明哺乳动物的再生能力可能会重新唤醒。
加丁纳说:“这将是我们人类可以再生的一天。”他的研究重点不是重建肢体,而是治疗瘫痪,生长健康的器官,甚至通过修复受损和破旧的组织来逆转衰老。他说:“当他们写下这个故事时,它将回到这些模型生物身上。”
但是,到那天的时候,野生的a可能已经消失了。这令加迪纳(Gardiner)和桑多瓦尔(Sandoval Guzm谩n)感到担忧,因为他们研究的动物(如许多实验动物)是高度近交的。科学家使用“育种系数”来衡量基因库的大小。同卵双胞胎的系数为100%;完全无关的个人得分接近零。分数超过12%表示该人口中大多数人都是与他们的表亲繁殖,并且被生态学家和遗传学家严重关注。十七世纪著名的近亲和不健康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系数通常在20%以上。a的平均近交系数为35%。
我们拥有的这些动物,它们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它们可以正常繁殖。但是它们是如此近交。这是一个瓶颈,加迪纳说。“自交系的种群非常容易患病。”
它们的近亲繁殖水平很高,部分原因是圈养tive徒采取了奇怪的历史道路。大多数实验室标本的起源可追溯到1863年由法国资助的远征队从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带走的34只动物中。他们在博物馆和博物学家的陪同下在欧洲掀起了狂热的狂热。
1935年,其中一些动物从波兰实验室返回北美,并最终成为纽约布法罗大学的繁殖基地。在这里,科学家们引入了一系列野生x来混合基因库,甚至还加入了虎((Ambystoma tigrinum)。布法罗人口蓬勃发展,并最终移居至列克星敦的肯塔基大学,该大学现已成为全球a育种的中心。这意味着,除了近交外,当今实验室和水族馆中的几乎所有a都实际上是老虎sal的一部分。
肯塔基州该计划的负责人兰德尔·沃斯(Randal Voss)说:“肯定会在欧洲遇到瓶颈,然后又出现了瓶颈。”该计划拥有大约2,000只成年成年人和3,000到1,000只幼虫。
沃斯说,得益于现代遗传学和干细胞研究,当今的x研究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2015年,他和他的小组发表了x基因组4的初始装配,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的规模很大,估计约有320亿个碱基。但这是不完全的-基因组的大小和复杂性被证明对Voss小组可以发挥的计算能力太大了。一些中心的科学家继续努力完成这张照片。
但是,当他们致力于这一工作时,这种生物对疾病的脆弱性已经在沃斯的设施中造成了神秘的大规模死亡。科学家担心,如果一种新的传染病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竞赛,可能会迫使他们放弃a,可能会使研究推迟数年。
而且,没有人能确定实验室a已经与野生的a分离得如此之多,以致失去了再生的关键要素。Sandoval Guzm谩n说:“回头研究野生种群可以为您提供不同的机制或不同的基因。”“破坏遗传多样性”当然是科学的损失。
两位数
“泪可以永远肯定知道,但是肯塔基州的a确实有一些区别,”阿图罗·维加拉·伊格莱西亚斯(Arturo Vergara Iglesias)说,凝视着懒洋洋地爬行的a。尽管他们将血统追溯到肯塔基大学的繁育设施,但他遇到的许多非本地动物随后都会被实验室,宠物店和业余爱好者饲养,这可能会导致问题。“他们有很多畸形。例如,他们经常有太多的手指。
Vergara Iglesias是生物学和水产养殖研究中心(CIBAC)的一名生物学家,该中心是霍奇米尔科附近的一家x育种设施,希望保留一些野生系。在侧面,他繁殖了自己的野生a,卖给实验室和宠物分销商。他站在传统的霍奇米尔科农场土地(CHINAMPA)的a缸上,用作游客的教育设施。这些动物以及他出售的其他动物,是从距离该地块不远的水中抽出的32只动物饲养的。在墨西哥,the是一种珍贵的宠物,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它是无数墨西哥模因和纪念品的主题,甚至是墨西哥城的官方表情符号。
很难确切知道野外还剩下多少a。赞布拉诺(Zambrano)猜测,在2014年的上一次调查中,总数少于1,000,甚至少于500。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可能更具体。他无法筹集资金进行任何后续研究。他可以通过简单的人口普查获得资金,这对保护工作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赞布拉诺说,为拯救野生x,政策制定者必须解决其两个主要威胁。第一类是非本地鱼类,例如鲤鱼(Cyprinus carpio)和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是通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实施的计划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引入霍奇米尔科的,目的是使更多蛋白质进入当地饮食。赞布拉诺说,他已经绘制了仍存在a的地图。他设想将支付给当地渔民一个团队,以持续扫荡他们的鱼。尽管这并不能清除所有的鱼,但花费数十万美元,可能会给give提供一个重新建立自己的窗口。他的工作表明,a在卵期时最容易受到鲤鱼的侵害,在幼年时最容易受到罗非鱼的侵害,但同时表明,如果can能够长到一定的大小,它们仍然可以繁衍。
第二个威胁更加棘手。每次大雨充斥着城市老化的下水道系统时,处理设施都会将人为的废物释放到霍奇米尔科,并伴有氨,重金属和难以言喻的其他有毒化学物质。两栖动物部分通过其高渗透性的皮肤呼吸,因此容易受到这些常规污染源的污染。它在野外完全存在,证明了动物的韧性。
这些是复杂的问题,但并非无法解决。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无所事事的宣传计划和一些摄影机会外,还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拯救野生the。2013年,CIBAC释放了数千只x进行行为研究;其中一些幸存下来,甚至在第二年繁殖。这表明,如果将人工饲养的sal饲养到一定的大小,它们也许可以在野外壮成长。但是生物学家警告说,这并不意味着墨西哥应该开始将它们释放到运河中。
格里菲思说:“在释放威胁之前,在野外释放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渊源可能只是通过增加更多的鱼类食物而增加了鱼类的数量。”?/ p>
当格里菲斯(Griffiths)在2000年首次在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工作时,他的计划是制定一个繁殖计划,旨在将releasing释放到野外。但是,当他和他的墨西哥伙伴看到生态系统的状况时,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生态系统受到了污染,并被捕食者所包围。把a杀死到死似乎是没有意义的。成功的再引进,例如英国的池蛙(Pelophylax lessonae)或美国的地b sal(Cryptobranchus alleganiensis),都需要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管理并与社区合作。
如果我们在十年中每年有一百万美元,我们将为霍奇米尔科省钱。赞布拉诺说,与在这个城市花费的钱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10月的一个下午,Zambrano和一群志愿者聚集在UNAM校园附近的池塘旁,将十只实验室饲养的野生a放入一个受保护的池塘中。如果动物存活并繁殖,它们有一天可能会成为该生物体的一种遗传库。过去两年来,Zambrano一直在零星地释放和追踪动物,以了解它们的行为和生境偏好。迄今为止,他的工作表明sal比最原始的池塘更喜欢肮脏的池塘,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如果消除其他压力,a可能仍会在霍奇米尔科繁盛。同样,CIBAC正在繁殖野生型动物,以维护the的遗传多样性。但是,如果a没有合适的家,大多数研究人员都会说,不管他们做什么,在野外灭绝都是不可避免的。
赞布拉诺说:“如果我这样看,会感到沮丧。”“以另一种观点看待它”,即我正在竭尽全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自然551,286-289(2017)
 健康教育网
健康教育网